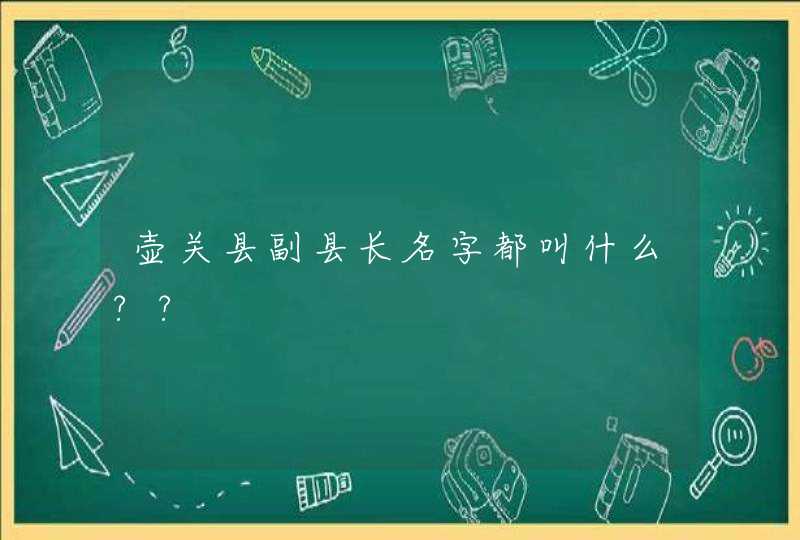
2011年4月 胡三虎:山西省壶关县人民 副县长,男,1966年出生,山西长治人
2011年5月7日上午,县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十九次会议,决定任命:卫 明为壶关县人民 常务副县长;赵文栋为壶关县人民 副县长。
王家胜为壶关县人民法院副院长、代理院长;张云骏为壶关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代理检察长。
长治市壶关县人民 机构信息
1、 领导成员名单
壶关县 领导:
县 长:马朝中
常务副县长:马先明
副县长:李志强 田兆伟 胡三虎 郭海英 冯宏声
党组成员:栗建平
壶关县 各部门主要负责人:
县 办公室主任:崔书华
发展和改革局局长:马光明
经贸局局长:秦志华
教育局局长:牛庆芳
科技局局长:田国庆
公安局局长:李寿昌
监察局局长 张君平
民政局局长 李建芳
司法局局长:牛忠平
财政局局长:郭太国
人事局局长:王买勤
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秦建明
城建局局长:王斌
交通局局长:郭刚德
水利局局长:
农业局局长:赵保忠
林业局局长:秦庆祥
卫生局局长:常安民
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局长:郭建国
审计局局长:赵红斌
县人民 工作部门:
国土资源局局长:杜学敏
县人民 直属机构:
环保局局长:魏根孝
统计局局长:闫宏斌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靳海棠
2、县 领导简历及分工
壶关县人民 县长:马朝中
简历:
马朝中,男,汉族,1957年1月出生,系山西省长治市人,1970年12月入伍参加工作,1975年5月入党,大学学历,现任长治市壶关县委副书记、县长。
1970年12月——1977年3月部队服役
1977年6月——1979年8月长治市供电局政工科干事
1979年9月——1983年8月山西大学历史系七九届学习,班党支部书记
1983年9月——1984年7月城区常青公司党委委员兼党办主任
1984年8月——1994年12 月市委组织部干事;市委办公厅副主任科员、秘书科长、办公室主任
1994年12月——1998年4月武乡县委常委、组织部长;1998年5月——2001年5月武乡县委副书记
2001年6月——2002年7月沁源县委副书记、县长
2002年7月——2005年3月城区区委副书记(正处)
2005年3月——今 任现职
分工:
主持县 工作和编委工作,全面负责经济工作,分管监委、人事局、财政局和审计局。
壶关县人民 副县长:马先明
简历:
马先明,男,汉族,1963年9月出生,山西省壶关县人,1984年10月加入中国 ,1982年10月参加工作,长治农校畜牧专业毕业,现任壶关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1982年10至1983年9月在壶关县林业局任干事;1983年10月至1993年1月任壶关县 办公室干事、副主任;1993年2月至1995年11月任壶关县石坡乡党委书记;1995年12月至2000年12月任壶关县西川底乡党委书记;2001年1月至2001年11月任壶关县委办公室主任;2001年12月至2006年6月任壶关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2006年7月至今任壶关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分工:
协助县长分管经贸、财税和安全工作。
分管经贸局、安监局、财政局、交通局、城镇集体企业联合社、中小企业局、粮食中心、县社、商贸总公司、外贸公司、长平公路公司;协调联系国税局、地税局、质监局、工商局、电力公司、煤运公司、煤焦站、公路段、人行、农行、工行、信用联社、银监办;联系县工会。
壶关县人民 副县长:李志强
简历:
李志强,男,汉族,大专文化程度,1956年11月出生,系长治县西火镇羊川村人,1972年2月参加工作,1974年12月入党。
具体分管:农业(林业、水利、国土、畜牧扶贫、供水、农经、农机、农技、气象)、民政、武装。
1972年2月至1974年12月,壶关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工作;
1975年1月至1980年1月,北京市卫戍区警卫一师服役;
1980年2月至1984年1月,壶关县公安局办公室工作;1984年2月至1984年6月,树掌公社副主任;
1984年7月至1985年1月,树掌镇副镇长;
1985年2月至1987年3月,树掌镇党委副书记;
1987年4月至1989年4月,树掌镇镇长;
1989年4月至1993年1月,黄山乡乡长、党委书记;1993年2月至1995年12月,常行乡党委书记;
1995年12月至1997年8月,百尺镇党委书记;
1997年8月至1998年5月,城关镇党委书记;
1998年5月至今,壶关县人民 副县长。
分工:
协助县长分管农业、民政和武装工作。
分管农业局、林业局(绿委办)、水利局、畜牧中心、国土资源局、农机中心、农技中心、农经中心、扶贫办、供水处和民政局;协调联系气象局。
壶关县人民 副县长:田兆伟
简历:
田兆伟,男,汉族,大学文化,1964年8月出生,系山西省阳城县人,1984年7月参加工作,1989年12月加入中国 ,现任壶关县人民 副县长。
田兆伟同志1982年9月至1984年7月,在山西省财贸学校读书;1984年7月毕业后,分配在市工商局参加工作,曾任办事员、科员、市工商学会副秘书长;1991年9月至1993年7月, 中央党校政治学专业本科毕业;1993年至2001年在市 办公厅工作,先期从事领导秘书工作,1997年起任市 办公厅社会科科长;2001年12月至今,任壶关县人民 副县长,具体分管文化、教育、计生等方面工作,2006年调整为分管计划、政法工作。
分工:
协助县长分管计划、城建工作。
分管公安局、司法局、发改局(物价局) 、城建局、环保局、统计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档案馆、物资总公司;联系检察院、法院。
壶关县人民 副县长:胡三虎
简历:
胡三虎,男,1966年出生,山西长治县人。
党员,大学文化,经济学学士,经济师,现任壶关县人民 副县长。
1984年9月——1988年7月,在山西经济管理学院计划统计系学习。
1988年7月——1992年11月,在山西省长治市统计局工作。
1992年11月——2003年5月,在长治高新区管委会工作,任办公室副主任、主任。
2003年5月——至今,任壶关县人民 副县长。
分工:
协助县长分管教育、文化、计生、 工作。
分管 办、教育局、计生局、文化中心、体育中心、广电中心、机关后勤中心、政务大厅、宾馆、交警队、 局、协调联系邮政局、网通公司、移动公司;联系史志办、文联、团委。
壶关县人民 副县长:郭海英
简历:
郭海英,女,汉族,1965年10月出生,大学本科文化,系壶关县龙泉镇川底村人。
1984年7月毕业于晋东南医专;
1984年9月在县医院参加工作;
2000年3月至2001年1月任县医院内科主任;
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任县医院副院长;
2003年6月至今任县 副县长。
分工:
协助县长分管卫生、科技、残联和老龄工作。
分管卫生局(爱卫办)、科技局、卫生监督所、疾控中心、县医院、地震局、老龄委、药材公司;协调联系食药局、石油公司、烟草公司、财保公司、人保公司;联系残联、妇联、科协。
壶关县人民 副县长:冯宏声
分工:
协助分管县长负责扶贫、旅游工作,协调联系新华书店。
壶关县人民 党组成员:栗建平
分工:
协助县长分管旅游工作,分管旅游中心。
韦唯道出“临心事”
这场名誉权官司的导火线是在一年多前点燃的。
1991年1月16日,南阳《声屏周报》头版发表了该报记者汤生午的采访文章,题为《有人说她得了可怕的病,有人干脆说她已经自杀,舆论莫衷一是。著名歌星韦唯接受本报电话采访道出其中原因》。文章借韦唯之口,“伤心地道出了她从不愿向外人多讲”的委屈:1、在1990年亚运会期间的一次演出中,十年前以一曲《乡恋》而名噪内地的某位乐团领导,不知心怀何意但却明显险恶地抓起话筒,向在座各位愤愤宣告了一个大胆的谣言:韦唯得爱滋病了。舆论哗然;2、韦唯的工资被无故停发已一年;3、作为国家一级演员,韦唯正常的医疗费这位领导却不准报销;4、文化部分给团里三位演员三套住房,其中明确指示要考虑分给韦唯一套。实际结果,不但同韦唯毫不沾边,而且这三套房子全上到了该领导个人的户口上;5、国外几家电视台通过文化部对韦唯的演出邀请,在各方都通过的情况下,却被这位领导一人无理拒绝;6、该领导对韦唯说,你走吧,离开这里我们也许才好相处,但走的方式更是其用意“特殊”。她希望韦唯走,一是去国外,二是辞职。如果想调走,那请拿10万元钱来;7、记者的一位同事曾得到过这位领导的明确相告:我就是要整韦唯!怎么了?“***”要整个人还不容易……
文章发表后,《声屏周报》社将报纸寄向与之联网的二百余家地方报纸,并在文章的旁边标明“请转载”字样。到1991年5月,全国各省市数十家报纸先后予以转载。
李谷一聘请律师诉诸法院
汤文的发表,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文章发表后,李谷一接连不断地接到质问、质询的电话和信件;更有恶言相加的辱骂。为了平息风波,为自己正名,李谷一在京召开了有四十多家新闻单位参加的新闻发布会。然后,李谷一又聘请律师为其诉讼代理人,于1992年1月向南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状告汤生午及《声屏周报》社侵犯其名誉权。
韦唯多变的诉讼地位
本案中,韦唯是个极其关键的人物。因为文章是以韦唯的口吻写的,并且在发表前,又经韦唯两次审稿,内容又都是韦唯的个人经历。因此,如何确认韦唯在案件中的诉讼地位,成了本案的一大难题:证人,第三人,抑或共同被告?如作证人,那案件的胜败与韦唯基本无关;如作第三人,那对韦唯不利,万一汤生午一方败诉,韦唯也只好跟着落败;而如果作为被告,那韦唯败诉后将承担法律责任。但让一个提供消息者承担法律责任,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似乎没有先例,李谷一在起诉书中并未将韦唯列为共同被告也许正是出于这一考虑。然而,南阳地区中级法院在对本案作了一番调查取证后,于1992年6月3日决定追加韦唯为共同被告。
韦唯诉讼地位的改变,预示着法院认为在整个纠纷过程中,韦唯负有一定责任,并有可能承担由此而来的法律后果。并且,韦唯从证人到被告人身份的变化,将使被告一方失去一个至关重要的证人,还使韦唯在法庭上所作的陈述的客观真实性大打折扣。这对被告人汤生午及《声屏周报》社是显然不利的。
但富有戏剧性变化的是,就在开庭的前夕,法院又突然决定正式撤销韦唯被追加的被告人身份,据云是“依据不足”。
这样,韦唯终于没有走向被告席。但这是否意味着原被告双方在本案中的诉讼命运有了某种转机呢?这仍是一个谜。
扑朔迷离,法院终于开庭审理
1992年7月8日,南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理本案。
在此之前,法院曾在北京就此案进行了调解。就在开庭前夕,法院在郑州又就此案作了一番调解。但由于双方分歧太大,调解根本无法达成协议。
出人意料的是,就在数百名记者云集宛城、准备采访李谷一名誉权案的庭审经过时,法院门口又突然贴出了本案延期审理的公告。个中原因.据说是法院准备就此案进行第三次调解。
两天之后。1992年7月10,南阳中院又作出了开庭审理的决定。
早晨7点刚过,法院门口就聚满了前来旁听的群众。刚竣工的审判庭,是一座四层楼共2500多平方米的建筑。正门上方,高悬着耀眼的国徽。四根粗大的黑色大理石柱子,给人以威严。庄重之感,仿佛昭示着法律的神圣。
上午8时30分,薄施粉黛、身着宝蓝色套裙的李谷一在丈夫肖卓能的陪同下来到法庭。被告汤生午、《声屏周报》法定代表人王根礼以及双方的代理律师巩沙、李大进,窦柏林、侯金海等人也先后出庭就坐。
在开庭的前一天,李谷一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表示,面对法庭,她很害怕,这会影响到自己的前半生和后半生。她始终认为汤生午的文章从头到尾都是失实的,正因为这样,她才来打官司。如果汤生午说的基本属实,只是枝节部分有问题,她是不会起诉的。在谈到韦唯时,李谷一说,她不明白韦唯为什么要发这个难,把话说得那么恶。最后,李谷一还对记者表示,如果她确实不对,有错误,她愿意向全国人民道歉。
在此之前,汤生午也曾信心十足地对记者说:“我认为开庭的话我能胜诉!但最终的结果不是我个人所能决定的。”
原告的指控与被告的答辩
审判长在宣布法庭纪律后,按照法定程序,由原告方宣读起诉书。
李谷一在起诉书中指出:原告方采用或是捏造、或是歪曲的手法,对她的名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这是“文革”以来演艺界最大的一次事件,是“四人帮”暴虐的重演,她要求被告方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18万元。并且,这个赔偿数额还不包括这次专程来南阳参加诉讼的费用,因为这笔帐目前还无法结算。
针对李谷一的指控,被告汤生午辩称,由于社会上关于韦唯的流传很多,作为一个记者有责任为一个青年演员澄清事实,因而经报社领导同意,对韦唯作了电话采访。文章写出后两次寄韦唯审查,所写内容都有正确的消息来源。
王根礼主编在答辩时认为,汤生午撰写的是人物专访文章,其基本内容真实。这篇文章在社会上起到了扶正压邪、伸张正义的作用,使外界有关韦唯的谣言消失,韦唯得以重回舞台。他还指责李谷一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身份,召开新闻发布会,向被告方施加压力,使《声屏周报》在政治上、经济上蒙受重大损失。
紧接着,法庭就汤生午文章所涉及李谷一的内容,依次就李谷一宣告韦唯得爱滋病以及在工资、住房、医疗费报销、出国演出等非难韦唯的问题逐一进行调查。
上午11时,审判长宣布休庭。
韦唯出庭作证
下午3时,法庭继续开庭审理。
梳着长辫、一身素装的著名歌星韦唯作为证人被传唤出庭作证。
首先由审判长对韦唯发问。
审判长:“韦唯,你提供的内容与文章是否一致?”
韦唯:“我当时向报社提供的确是这些问题,应该说是一致的。”
审判长:“有否失实的地方?”
韦唯:“李谷一说我得爱滋病,是在一次彩排时,而不是在演出时。”
审判长:“关于房子问题是怎么回事?”
韦唯:“去老山慰问演出时,我们几个演员向文化部领导提出要求解决住房,领导同意批给我们。我回京后打了报告,听说部里批下来几间房,其中有我的住房。我向李谷一要新房钥匙,她拒绝。我得到确切的消息,李谷一得了三套房子。”
审判长:“工资问题是怎么回事?”
韦唯:“1990年6月,我在与李谷一谈话时,她说把我工资停了,我吃惊。李谷一说这样做好管理。我想去领4、5月份的工资,可是从4月份起已经停了,直到现在还停发。”
对于韦唯所作的证词,李谷一当庭表示异议:“韦唯的证词完全不属实!”
韦唯也毫不相让:“我的证词完全属实,我亲身的经历就是证据!”
接着,原告代理律师向韦唯提出了一连串的提问。
下午5时,韦唯作证完毕。
李谷一是否说过韦唯得爱滋病?
1992年7月11日。法庭在经过一天的调查后,进人辩论阶段。
由于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汤生午文章的内容是否属实,而汤文的主要内容是涉及到李谷一是否大庭广众面前散布韦唯得了爱滋病。因此,原、被告双方首先就这一问题展开“拉锯战”。
原告代理人认为:1990年亚运会期间,中国轻音乐团共演出三场,时间是1990年9月25日至27日晚,地点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参加演出的有关人员及个别观众证实,三场演出中从未出现过李谷一抓过话筒宣布韦唯得爱滋病的情节。法庭上,韦唯也承认不是在演出期间,而是在亚运会演出的一次彩排中。并且,有证据证明,当时李谷一只是以询问的语气问她,是出于对韦唯的关心,而根本不像被告人所写的“不知心怀何意但却明显险恶地抓起话筒,向在座各位愤愤宣告了一个大胆的谣言:韦唯得爱滋病了。”
对此,被告方代理人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并列举一系列的证据来证明李谷一确在公共场合散布过韦唯得爱滋病的谣言。
1、证人韦唯在回答法院询问时称:“1990年9月24日排练时,李谷一在台下拿着话筒指挥,我上台时也拿着话筒,我有个习惯爱挠头,当时团长就用话筒说:‘你挠什么头,你那个爱滋病掉下来传给别人怎么办?’我听后很别扭,也没吭声。我唱一小节后,就拿着话筒说了一句:‘你还说呢,人家已经告诉我,说是你们俩说出来的(指李谷一夫妇二人)。’我一说,她更厉害了,说:‘谁说的,谁说的?’我说:‘反正有人说。”’
2、卷三P178页。证人陈玉生证言:“在1990年7月份我被抽到亚运全组委会文展部,在演出处工作。……9月24日下午,韦唯上场,右手拿着话筒,从下场门往上场门走时,她的左手挠了挠头,这时李谷一就拿着无线话筒喊:‘韦唯你不要再挠了,别把爱滋病掉在舞台上,传染我们团的人。’这时韦唯拿着话筒说:‘我告诉你,李谷一,现在外面说我得爱滋病这事都是你给造的谣。’李谷一说:‘谁说的?’韦唯说:‘有三、四个人都告诉我。”’
3、卷三P96页。轻音乐团乐队队长王春生证明说:“韦唯在台上挠脑袋,李说:‘你别老挠脑袋,外边都说你得爱滋病了。’接着韦唯说:‘我知道外边说我得爱滋病都是你说的。’李说:‘谁说的,叫出来对质。”’
4、原告本人也承认说过此话。在1992年5月20日法院调查李谷一笔录中,李说:“韦唯唱第一支歌后用手挠头(乐队正在找谱子的时候),这时我在台下,我用话筒对韦唯讲:‘韦唯,你别挠了,你现在身体情况怎样,外面传你得了这个病、那个病,你注意一点,别人说你得了爱滋病。”’
以上包括李谷一本人在内的共18人(其中原告提供的8个证人)都证明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原告李谷一确实在大庭广众面前说过韦唯得爱滋病的话。
但是,原告李谷一却说:“我这样问韦唯是对她的关心。”
所谓有不准确之处,就是在于原告人的话不是在亚运会演出之中,而是在亚运会彩排之时所说。关于这一点,作者汤生午已在《编钟之声》作了纠正。
关于韦唯出国演出
原告代理人指出,整个调查过程中,没有发现“国外几家电视台通过文化部”邀请韦唯出国的有关证据。当然,应该说也就不存在“各方面都通过的情况下却被这位领导一人无理拒绝”的问题。事实是,1990年9月到10月,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下属的一家录音公司,曾出面商借韦唯前往爱尔兰演出。为此,轻音乐团领导于10月上旬作了专门研究,表示同意韦唯出国,但有些责任和技术性的问题必须由派出单位承担或解决。团里向部里打了报告,请求批准韦唯出国之行。在这期间,李谷一一直在百忙之中让团里人事处向部里催办,但由于某种客观原因使韦唯这次出国未能成行。从现有的证据看,李谷一对韦唯出国是持积极态度的,并不存在“无理拒绝”的问题。
对此,被告代理人仍认为,汤文的报道是千真万确的。
①卷四P43页有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90)中心发字第112号文向文化部所作的《关于组织韦唯等三人交流小组出访欧美五国的请示》。
②卷四P45页有我国驻英国、联邦德国、爱尔兰、休斯顿、法国五国使馆文化处表示同意韦唯等三人出访的意见。
③卷四P53-63页有文化交流中心提供的有关韦唯等三人出访的档案材料。
④证人李杰华、马光明证明和其他材料证实,为此事,交流中心先跟文化部艺术局方杰局长说,方杰给李谷一打了电话,李同意之后,中心向轻音乐团邀请,团里作了正式研究表示同意。
⑤人事处长田玉凤、原党支部书记褚鹤翔、艺术指导刘秉义证明他们和王建国、李谷一共同讨论过韦唯出访事宜,最后的意见是“同意韦唯出国访问”。
⑥艺术局外事处主管此事的冯树龙证明:如果团里明确同意韦唯出国,那我们就根据团里意见,办理政审手续,报外联局。”
以上大量事实证明,对韦唯出国一事,确系各方面都已通过。那么,是否被李谷一无理拒绝呢?以下事实可以说明:
①1991年10月15日李谷一曾以轻音乐团的名义为阻止韦唯出国向文化部艺术局发了《关于外单位借调我团韦唯出国的情况请示》。李在请示中写到:“……对此事我们感到相当为难,……对韦唯目前的思想和身体状况,我们不无担心。”报告中还具体写了韦唯思想不好的表现。报告自始至终没有表明“团里同意韦唯出国”的意见。这是个不同意韦唯出国的报告。
②卷三P8页。1992年5月19日李杰华证明说:“……李谷一隐瞒了一个事实,就是没有把团里确定的情况汇报给艺术局,局领导认为,轻音乐团对韦唯外出一事态度不明。李谷一是有责任的。”
③卷三P18页。1992年5月29日马文光证明:乐团支部大会开会同意韦唯出国。李谷一个人给艺术局打的报告没有证明同意韦唯出国。这个报告是李谷一以个人名义(注:盖的是团印)给艺术局写的建议。没有把大会通过的“同意韦唯出国”的决定报给艺术局。杰华老师明确指出她这个做法是错误的。”
④卷四P74页。1992年6月6日,音像出版社副社长,出国组组长江凌证明:“当时韦唯跟我谈到李谷一可能有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出面和李谷一协商,李谷一提出三条意见:第一,韦唯表现不好;第二,韦唯身体不好:第三.由交流中心支付一部分停演费。”
汤文说,李谷一“一人无理拒绝”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韦唯的分房问题
原告代理人指出,据文化部房管部门证实,1990年元月下旬,文化部将五套住房借给轻音乐团使用。地点是北京西坝河。这五套房子的分配权属于轻音乐团。其中两套做临时办公室,另三套分配给韦唯、鞠敬伟、黄卓三位女演员。不知何种原因,韦唯对所分住房不满意,拒绝在住房协议卜签字,因此没有住进去。不过,到目前为止,该套住房还仍为韦唯保留。文化部计财司房产处证实:“西坝河三号楼为北京市房产开发总公司的商品房,文化部计财司预先与房产总公司办理有关契约手续时,在办理轻音乐团的五套住房时,是我们用李谷一团长的名字签订了临时协议,为了单位领导承担应有的权利和义务,与李谷一同志的户口不发生任何牵连。”该部门还证明,“文化部从来不干涉所属院团的分房方案,中国轻音乐团的住房问题由该团自定。”由此,三个问题大白于天下:其一,并不是李谷一没有给韦唯住房,而是她自己不知何故没有办理居住手续;其二,文化部从来没有“明确指示”要分给韦唯一套住房,而分房由团里自行决定;其三,并不是“三套房子全上到了该领导个人的户口上”,而是文化部有关部门用李谷一的名字去办理了房屋归属的有关手续。是履行法定代表人的义务,是一种签字保证,与李谷一个人户口“毫不沾边”。
被告代理人认为,汤文关于韦唯住房问题上的内容,其基本事实是存在的,根据是:1、1992年5月22日韦唯回答法院询问时说:“……文化部××部长指示房子给我们三个人,此事我是后来跟艺术局领导谈话时知道的(是艺术局领导给计财司打电话我听到的)。高部长替我打电话让给我一套。李谷一跟我说有我一套,但没有给我住。我多次向李谷一要求,李说:‘你等着,等着,你不是要出国吗?’‘你的问题很多,以后再说。’“法院问韦唯:“你的住房手续办没有?”韦唯答:“没有,她不理我,她不给我,她说:‘你不是要出国吗,出了国再说。’我总是遭到拒绝。”
2、文化部计财司甄司长。艺术局党组办公室白主任证明:韦唯上述的证词是准确的。甄司长讲:“两年前,从西坝河给他们几套房子,当时口头上给李谷一说过给几个演员(韦唯、黄卓、鞠敬伟)考虑一下。分房时计财司没有文字戴帽,团里是怎样分的我们不了解。后来房产处汇报说:‘李谷一反映韦唯要出国,房子先不给她。”’
3、从房管部门一整套有关三套房子分配的档案材料来看,这三套房子确实记在了李谷一名下。
“无故扣发韦唯工资”
关于汤文所称无故扣发韦唯工资一事,原告代理人指出:
1989年12月27日,文化部批准了韦唯提出的自费赴瑞士旅游访友的申请。根据国家的有关政策,文化部的批复函中的确指示中国轻音乐团,对韦唯“假期期间停发工资”(见文化部艺人字[89]第326号函)。不知什么原因,韦唯未能出国,但也一直未到团里销假报到;近一年的时间与单位脱离联系。中国轻音乐团根据文化部、北京市以及团里的制度、规定,无正当理由逾假不归,可以停发工资或依旷职论,故此停发了韦唯工资。但停发的是10个月(截止到汤文发表之日)而不是一年。
被告代理人认为,李谷一的这一做法仍有不当之处。
1、1989年12月27日文化部艺人字(89)第326号《关于同意韦唯自费赴瑞士旅游的批复》称:“同意你团韦唯应黛安娜女士邀请自费赴瑞士旅游访友三个月,假期期间停发工资……”。而李谷一在3个月的假期(实际未出团)期间没有扣韦唯的工资,却在出国期外的10个月中扣了韦唯的工资。
2、韦唯在扣发工资期间(1990年4月至1991年1月),基本上在团内上班,这是有据可查的,因此,李谷一扣工资理属无故。原告说:1990年全团指令演出88场,韦唯只参加8场,因此应扣韦唯的工资。我们认为,这理由也不能成立:①每场演出不一定都应有韦唯参加;②韦唯的团外公益活动多,正如名医生坐班时间和一般医生就不一样;③轻音乐团管理混乱,无章可循。卷三P50页,1992年5月26日法院办案人员问田玉凤:“上边谈的扣发工资的做法团内有明文规定吗?”田答:“我们团管理混乱,没有什么文字制度,自费出国,团长同意后,交待谁出国了就停发谁的工资。”
法庭上的最后陈述
双方代理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上午的辩论一直持续到午后一点钟,审判长宣布休庭。
原告李谷一在下午的第二轮辩论中,嗓音哽咽,被告汤生午也显得异常激动。双方律师又继续进行了第二轮、第三轮的辩论。旁听席上,成千的听众一次又一次情不自禁地为双方精彩的论辩击掌叫好。
辩论结束后,双方当事人作最后陈述。
“我相信法院会公正处理。”李谷一如是说。
被告汤生午的最后陈述感慨激昂,使不少旁听者落下了眼泪。他在陈述中说:“我原想通过报道使错误的造成者会因此而内疚,然而我想错了,原告不但没有这样,反而更加肆无忌惮地且更大范围地加大对受害者的摧残,更广泛地散发谣言,看来,良好的愿望和良好的结果也许是不一致的。”
被告《声屏周报》主编王根礼在最后陈述中称:对于汤文中个别细节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希望审判长对新闻工作者所受的客观限制予以体谅。
法庭临近结束审理时,审判长询问原告李谷一是否愿意放弃或变更诉讼要求。李谷一说:“很抱歉,不放弃。”审判长再问原告是否愿意接受法庭调解,李谷一说:“由于被告表现不好,不同意调解。”
夜幕来临,审判长再次宣布休庭。
李谷一哭了
1992年7月12日。今天,李谷一名誉权案的一审结局将见分晓。一大早,法庭门外又聚集了数以千计的旁听群众。
直到上午9时30分,法庭才再次开庭。双方当事人在各自的位置上正襟危坐,焦急地等待着法庭的判决。
审判长宣读判决书。判决书很长,大致的意思是,在亚运会演出中,李谷一并未说过韦唯得爱滋病了。至于汤文的其他内容,法庭认为也基本失实。
根据上述认定,审判长宣布:“本庭认为被告报道基本内容失实,损害了原告李谷一的名誉,造成了后果,构成了侵害原告的名誉权。原告诉讼请求理由正当,应予支持”,并认定在这起案件中,《声屏周报》负有主要责任,汤生午“听信一面之词”,也有一定的责任。认为原告李谷一要求被告赔偿16万元损失和支付3000元抚慰金,超过必要合理部分不予支持。
法庭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判决如下:
“一、本院责令被告《声屏周报》和汤生午立即停止对原告李谷一名誉权的侵害;二、被告《声屏周报》和汤生午在《声屏周报》头版显要位置刊登向李谷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文章,所刊文章内容须经本院核准;三、被告《声屏周报》赔偿原告2000元,被告汤生午赔偿原告500元;四、被告《声屏周报》支付原告抚慰金400元,被告汤生午支付原告抚慰金10O元。案件受理费70元由两被告承担。”
听完判决,李谷一激动地哭了,而二位被告人则神情冷峻。旁听席上,没有人们预料中的掌声,这与前两天庭审中的热烈场面显得极不协调。
尽管不服,但未上诉
“这场官司现在还只是划了个逗号,还不是句号。判决并未给我带来喜悦,我的心情是沉重的。到南阳来打官司,我是挺而走险的。由于我的身份、地位,容易使人产生‘大原告、小被告’的想法,如果我赢,会被人认为有背景,如果我输,会被人认为活该。”
听得出,李谷一的语调是伤感的。
“我为这场官司已花了两万多元,因为我珍视艺术家的形象和名誉,这比金钱更宝贵。如果终审维持一审判决的话,我将把赔偿我的3000元捐给南阳的‘希望工程’。”
被告汤生午及《声屏周报》社对法院判决自然不服,但他们表示,这一结果早在意料之中。他们将向河南省高级法院提出上诉。王根礼还表示,如二审维持原判,他将提请检察院抗诉。
被告方的代理人李大进认为:一审判决有失公允,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比如有关爱滋病的传言,已有多人证言证实确系原告所说,虽然“亚运会演出”和“排练”有很大不同,但原告已构成事实并造成后果,这是不容否定的。怎么可以完全抹去呢?离开南阳时,李律师只说了这么一句颇为耐人寻味的话:“以后再不到南阳打官司了!”
被告汤生午的另一位律师窦柏林似乎亦有此同感:“本案结束后将给我的律师生涯划个句号。”
看来,轰动海内外的著名歌唱家李谷一名誉权案的最终结局,似乎还难以预料。但出人意料的是,尽管被告方对法院的判决表示不服,但权衡再三,他们最终未在法定的期限内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个中原因,颇为令人深思。
这场名誉权官司的导火线是在一年多前点燃的。
1991年1月16日,南阳《声屏周报》头版发表了该报记者汤生午的采访文章,题为《有人说她得了可怕的病,有人干脆说她已经自杀,舆论莫衷一是。著名歌星韦唯接受本报电话采访道出其中原因》。文章借韦唯之口,“伤心地道出了她从不愿向外人多讲”的委屈:1、在1990年亚运会期间的一次演出中,十年前以一曲《乡恋》而名噪内地的某位乐团领导,不知心怀何意但却明显险恶地抓起话筒,向在座各位愤愤宣告了一个大胆的谣言:韦唯得爱滋病了。舆论哗然;2、韦唯的工资被无故停发已一年;3、作为国家一级演员,韦唯正常的医疗费这位领导却不准报销;4、文化部分给团里三位演员三套住房,其中明确指示要考虑分给韦唯一套。实际结果,不但同韦唯毫不沾边,而且这三套房子全上到了该领导个人的户口上;5、国外几家电视台通过文化部对韦唯的演出邀请,在各方都通过的情况下,却被这位领导一人无理拒绝;6、该领导对韦唯说,你走吧,离开这里我们也许才好相处,但走的方式更是其用意“特殊”。她希望韦唯走,一是去国外,二是辞职。如果想调走,那请拿10万元钱来;7、记者的一位同事曾得到过这位领导的明确相告:我就是要整韦唯!怎么了?“***”要整个人还不容易……
文章发表后,《声屏周报》社将报纸寄向与之联网的二百余家地方报纸,并在文章的旁边标明“请转载”字样。到1991年5月,全国各省市数十家报纸先后予以转载。
李谷一聘请律师诉诸法院
汤文的发表,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文章发表后,李谷一接连不断地接到质问、质询的电话和信件;更有恶言相加的辱骂。为了平息风波,为自己正名,李谷一在京召开了有四十多家新闻单位参加的新闻发布会。然后,李谷一又聘请律师为其诉讼代理人,于1992年1月向南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状告汤生午及《声屏周报》社侵犯其名誉权。
韦唯多变的诉讼地位
本案中,韦唯是个极其关键的人物。因为文章是以韦唯的口吻写的,并且在发表前,又经韦唯两次审稿,内容又都是韦唯的个人经历。因此,如何确认韦唯在案件中的诉讼地位,成了本案的一大难题:证人,第三人,抑或共同被告?如作证人,那案件的胜败与韦唯基本无关;如作第三人,那对韦唯不利,万一汤生午一方败诉,韦唯也只好跟着落败;而如果作为被告,那韦唯败诉后将承担法律责任。但让一个提供消息者承担法律责任,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似乎没有先例,李谷一在起诉书中并未将韦唯列为共同被告也许正是出于这一考虑。然而,南阳地区中级法院在对本案作了一番调查取证后,于1992年6月3日决定追加韦唯为共同被告。
韦唯诉讼地位的改变,预示着法院认为在整个纠纷过程中,韦唯负有一定责任,并有可能承担由此而来的法律后果。并且,韦唯从证人到被告人身份的变化,将使被告一方失去一个至关重要的证人,还使韦唯在法庭上所作的陈述的客观真实性大打折扣。这对被告人汤生午及《声屏周报》社是显然不利的。
但富有戏剧性变化的是,就在开庭的前夕,法院又突然决定正式撤销韦唯被追加的被告人身份,据云是“依据不足”。
这样,韦唯终于没有走向被告席。但这是否意味着原被告双方在本案中的诉讼命运有了某种转机呢?这仍是一个谜。
扑朔迷离,法院终于开庭审理
1992年7月8日,南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理本案。
在此之前,法院曾在北京就此案进行了调解。就在开庭前夕,法院在郑州又就此案作了一番调解。但由于双方分歧太大,调解根本无法达成协议。
出人意料的是,就在数百名记者云集宛城、准备采访李谷一名誉权案的庭审经过时,法院门口又突然贴出了本案延期审理的公告。个中原因.据说是法院准备就此案进行第三次调解。
两天之后。1992年7月10,南阳中院又作出了开庭审理的决定。
早晨7点刚过,法院门口就聚满了前来旁听的群众。刚竣工的审判庭,是一座四层楼共2500多平方米的建筑。正门上方,高悬着耀眼的国徽。四根粗大的黑色大理石柱子,给人以威严。庄重之感,仿佛昭示着法律的神圣。
上午8时30分,薄施粉黛、身着宝蓝色套裙的李谷一在丈夫肖卓能的陪同下来到法庭。被告汤生午、《声屏周报》法定代表人王根礼以及双方的代理律师巩沙、李大进,窦柏林、侯金海等人也先后出庭就坐。
在开庭的前一天,李谷一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表示,面对法庭,她很害怕,这会影响到自己的前半生和后半生。她始终认为汤生午的文章从头到尾都是失实的,正因为这样,她才来打官司。如果汤生午说的基本属实,只是枝节部分有问题,她是不会起诉的。在谈到韦唯时,李谷一说,她不明白韦唯为什么要发这个难,把话说得那么恶。最后,李谷一还对记者表示,如果她确实不对,有错误,她愿意向全国人民道歉。
在此之前,汤生午也曾信心十足地对记者说:“我认为开庭的话我能胜诉!但最终的结果不是我个人所能决定的。”
原告的指控与被告的答辩
审判长在宣布法庭纪律后,按照法定程序,由原告方宣读起诉书。
李谷一在起诉书中指出:原告方采用或是捏造、或是歪曲的手法,对她的名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这是“文革”以来演艺界最大的一次事件,是“四人帮”暴虐的重演,她要求被告方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18万元。并且,这个赔偿数额还不包括这次专程来南阳参加诉讼的费用,因为这笔帐目前还无法结算。
针对李谷一的指控,被告汤生午辩称,由于社会上关于韦唯的流传很多,作为一个记者有责任为一个青年演员澄清事实,因而经报社领导同意,对韦唯作了电话采访。文章写出后两次寄韦唯审查,所写内容都有正确的消息来源。
王根礼主编在答辩时认为,汤生午撰写的是人物专访文章,其基本内容真实。这篇文章在社会上起到了扶正压邪、伸张正义的作用,使外界有关韦唯的谣言消失,韦唯得以重回舞台。他还指责李谷一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身份,召开新闻发布会,向被告方施加压力,使《声屏周报》在政治上、经济上蒙受重大损失。
紧接着,法庭就汤生午文章所涉及李谷一的内容,依次就李谷一宣告韦唯得爱滋病以及在工资、住房、医疗费报销、出国演出等非难韦唯的问题逐一进行调查。
上午11时,审判长宣布休庭。
韦唯出庭作证
下午3时,法庭继续开庭审理。
梳着长辫、一身素装的著名歌星韦唯作为证人被传唤出庭作证。
首先由审判长对韦唯发问。
审判长:“韦唯,你提供的内容与文章是否一致?”
韦唯:“我当时向报社提供的确是这些问题,应该说是一致的。”
审判长:“有否失实的地方?”
韦唯:“李谷一说我得爱滋病,是在一次彩排时,而不是在演出时。”
审判长:“关于房子问题是怎么回事?”
韦唯:“去老山慰问演出时,我们几个演员向文化部领导提出要求解决住房,领导同意批给我们。我回京后打了报告,听说部里批下来几间房,其中有我的住房。我向李谷一要新房钥匙,她拒绝。我得到确切的消息,李谷一得了三套房子。”
审判长:“工资问题是怎么回事?”
韦唯:“1990年6月,我在与李谷一谈话时,她说把我工资停了,我吃惊。李谷一说这样做好管理。我想去领4、5月份的工资,可是从4月份起已经停了,直到现在还停发。”
对于韦唯所作的证词,李谷一当庭表示异议:“韦唯的证词完全不属实!”
韦唯也毫不相让:“我的证词完全属实,我亲身的经历就是证据!”
接着,原告代理律师向韦唯提出了一连串的提问。
下午5时,韦唯作证完毕。
李谷一是否说过韦唯得爱滋病?
1992年7月11日。法庭在经过一天的调查后,进人辩论阶段。
由于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汤生午文章的内容是否属实,而汤文的主要内容是涉及到李谷一是否大庭广众面前散布韦唯得了爱滋病。因此,原、被告双方首先就这一问题展开“拉锯战”。
原告代理人认为:1990年亚运会期间,中国轻音乐团共演出三场,时间是1990年9月25日至27日晚,地点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参加演出的有关人员及个别观众证实,三场演出中从未出现过李谷一抓过话筒宣布韦唯得爱滋病的情节。法庭上,韦唯也承认不是在演出期间,而是在亚运会演出的一次彩排中。并且,有证据证明,当时李谷一只是以询问的语气问她,是出于对韦唯的关心,而根本不像被告人所写的“不知心怀何意但却明显险恶地抓起话筒,向在座各位愤愤宣告了一个大胆的谣言:韦唯得爱滋病了。”
对此,被告方代理人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并列举一系列的证据来证明李谷一确在公共场合散布过韦唯得爱滋病的谣言。
1、证人韦唯在回答法院询问时称:“1990年9月24日排练时,李谷一在台下拿着话筒指挥,我上台时也拿着话筒,我有个习惯爱挠头,当时团长就用话筒说:‘你挠什么头,你那个爱滋病掉下来传给别人怎么办?’我听后很别扭,也没吭声。我唱一小节后,就拿着话筒说了一句:‘你还说呢,人家已经告诉我,说是你们俩说出来的(指李谷一夫妇二人)。’我一说,她更厉害了,说:‘谁说的,谁说的?’我说:‘反正有人说。”’
2、卷三P178页。证人陈玉生证言:“在1990年7月份我被抽到亚运全组委会文展部,在演出处工作。……9月24日下午,韦唯上场,右手拿着话筒,从下场门往上场门走时,她的左手挠了挠头,这时李谷一就拿着无线话筒喊:‘韦唯你不要再挠了,别把爱滋病掉在舞台上,传染我们团的人。’这时韦唯拿着话筒说:‘我告诉你,李谷一,现在外面说我得爱滋病这事都是你给造的谣。’李谷一说:‘谁说的?’韦唯说:‘有三、四个人都告诉我。”’
3、卷三P96页。轻音乐团乐队队长王春生证明说:“韦唯在台上挠脑袋,李说:‘你别老挠脑袋,外边都说你得爱滋病了。’接着韦唯说:‘我知道外边说我得爱滋病都是你说的。’李说:‘谁说的,叫出来对质。”’
4、原告本人也承认说过此话。在1992年5月20日法院调查李谷一笔录中,李说:“韦唯唱第一支歌后用手挠头(乐队正在找谱子的时候),这时我在台下,我用话筒对韦唯讲:‘韦唯,你别挠了,你现在身体情况怎样,外面传你得了这个病、那个病,你注意一点,别人说你得了爱滋病。”’
以上包括李谷一本人在内的共18人(其中原告提供的8个证人)都证明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原告李谷一确实在大庭广众面前说过韦唯得爱滋病的话。
但是,原告李谷一却说:“我这样问韦唯是对她的关心。”
所谓有不准确之处,就是在于原告人的话不是在亚运会演出之中,而是在亚运会彩排之时所说。关于这一点,作者汤生午已在《编钟之声》作了纠正。
关于韦唯出国演出
原告代理人指出,整个调查过程中,没有发现“国外几家电视台通过文化部”邀请韦唯出国的有关证据。当然,应该说也就不存在“各方面都通过的情况下却被这位领导一人无理拒绝”的问题。事实是,1990年9月到10月,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下属的一家录音公司,曾出面商借韦唯前往爱尔兰演出。为此,轻音乐团领导于10月上旬作了专门研究,表示同意韦唯出国,但有些责任和技术性的问题必须由派出单位承担或解决。团里向部里打了报告,请求批准韦唯出国之行。在这期间,李谷一一直在百忙之中让团里人事处向部里催办,但由于某种客观原因使韦唯这次出国未能成行。从现有的证据看,李谷一对韦唯出国是持积极态度的,并不存在“无理拒绝”的问题。
对此,被告代理人仍认为,汤文的报道是千真万确的。
①卷四P43页有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90)中心发字第112号文向文化部所作的《关于组织韦唯等三人交流小组出访欧美五国的请示》。
②卷四P45页有我国驻英国、联邦德国、爱尔兰、休斯顿、法国五国使馆文化处表示同意韦唯等三人出访的意见。
③卷四P53-63页有文化交流中心提供的有关韦唯等三人出访的档案材料。
④证人李杰华、马光明证明和其他材料证实,为此事,交流中心先跟文化部艺术局方杰局长说,方杰给李谷一打了电话,李同意之后,中心向轻音乐团邀请,团里作了正式研究表示同意。
⑤人事处长田玉凤、原党支部书记褚鹤翔、艺术指导刘秉义证明他们和王建国、李谷一共同讨论过韦唯出访事宜,最后的意见是“同意韦唯出国访问”。
⑥艺术局外事处主管此事的冯树龙证明:如果团里明确同意韦唯出国,那我们就根据团里意见,办理政审手续,报外联局。”
以上大量事实证明,对韦唯出国一事,确系各方面都已通过。那么,是否被李谷一无理拒绝呢?以下事实可以说明:
①1991年10月15日李谷一曾以轻音乐团的名义为阻止韦唯出国向文化部艺术局发了《关于外单位借调我团韦唯出国的情况请示》。李在请示中写到:“……对此事我们感到相当为难,……对韦唯目前的思想和身体状况,我们不无担心。”报告中还具体写了韦唯思想不好的表现。报告自始至终没有表明“团里同意韦唯出国”的意见。这是个不同意韦唯出国的报告。
②卷三P8页。1992年5月19日李杰华证明说:“……李谷一隐瞒了一个事实,就是没有把团里确定的情况汇报给艺术局,局领导认为,轻音乐团对韦唯外出一事态度不明。李谷一是有责任的。”
③卷三P18页。1992年5月29日马文光证明:乐团支部大会开会同意韦唯出国。李谷一个人给艺术局打的报告没有证明同意韦唯出国。这个报告是李谷一以个人名义(注:盖的是团印)给艺术局写的建议。没有把大会通过的“同意韦唯出国”的决定报给艺术局。杰华老师明确指出她这个做法是错误的。”
④卷四P74页。1992年6月6日,音像出版社副社长,出国组组长江凌证明:“当时韦唯跟我谈到李谷一可能有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出面和李谷一协商,李谷一提出三条意见:第一,韦唯表现不好;第二,韦唯身体不好:第三.由交流中心支付一部分停演费。”
汤文说,李谷一“一人无理拒绝”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韦唯的分房问题
原告代理人指出,据文化部房管部门证实,1990年元月下旬,文化部将五套住房借给轻音乐团使用。地点是北京西坝河。这五套房子的分配权属于轻音乐团。其中两套做临时办公室,另三套分配给韦唯、鞠敬伟、黄卓三位女演员。不知何种原因,韦唯对所分住房不满意,拒绝在住房协议卜签字,因此没有住进去。不过,到目前为止,该套住房还仍为韦唯保留。文化部计财司房产处证实:“西坝河三号楼为北京市房产开发总公司的商品房,文化部计财司预先与房产总公司办理有关契约手续时,在办理轻音乐团的五套住房时,是我们用李谷一团长的名字签订了临时协议,为了单位领导承担应有的权利和义务,与李谷一同志的户口不发生任何牵连。”该部门还证明,“文化部从来不干涉所属院团的分房方案,中国轻音乐团的住房问题由该团自定。”由此,三个问题大白于天下:其一,并不是李谷一没有给韦唯住房,而是她自己不知何故没有办理居住手续;其二,文化部从来没有“明确指示”要分给韦唯一套住房,而分房由团里自行决定;其三,并不是“三套房子全上到了该领导个人的户口上”,而是文化部有关部门用李谷一的名字去办理了房屋归属的有关手续。是履行法定代表人的义务,是一种签字保证,与李谷一个人户口“毫不沾边”。
被告代理人认为,汤文关于韦唯住房问题上的内容,其基本事实是存在的,根据是:1、1992年5月22日韦唯回答法院询问时说:“……文化部××部长指示房子给我们三个人,此事我是后来跟艺术局领导谈话时知道的(是艺术局领导给计财司打电话我听到的)。高部长替我打电话让给我一套。李谷一跟我说有我一套,但没有给我住。我多次向李谷一要求,李说:‘你等着,等着,你不是要出国吗?’‘你的问题很多,以后再说。’“法院问韦唯:“你的住房手续办没有?”韦唯答:“没有,她不理我,她不给我,她说:‘你不是要出国吗,出了国再说。’我总是遭到拒绝。”
2、文化部计财司甄司长。艺术局党组办公室白主任证明:韦唯上述的证词是准确的。甄司长讲:“两年前,从西坝河给他们几套房子,当时口头上给李谷一说过给几个演员(韦唯、黄卓、鞠敬伟)考虑一下。分房时计财司没有文字戴帽,团里是怎样分的我们不了解。后来房产处汇报说:‘李谷一反映韦唯要出国,房子先不给她。”’
3、从房管部门一整套有关三套房子分配的档案材料来看,这三套房子确实记在了李谷一名下。
“无故扣发韦唯工资”
关于汤文所称无故扣发韦唯工资一事,原告代理人指出:
1989年12月27日,文化部批准了韦唯提出的自费赴瑞士旅游访友的申请。根据国家的有关政策,文化部的批复函中的确指示中国轻音乐团,对韦唯“假期期间停发工资”(见文化部艺人字[89]第326号函)。不知什么原因,韦唯未能出国,但也一直未到团里销假报到;近一年的时间与单位脱离联系。中国轻音乐团根据文化部、北京市以及团里的制度、规定,无正当理由逾假不归,可以停发工资或依旷职论,故此停发了韦唯工资。但停发的是10个月(截止到汤文发表之日)而不是一年。
被告代理人认为,李谷一的这一做法仍有不当之处。
1、1989年12月27日文化部艺人字(89)第326号《关于同意韦唯自费赴瑞士旅游的批复》称:“同意你团韦唯应黛安娜女士邀请自费赴瑞士旅游访友三个月,假期期间停发工资……”。而李谷一在3个月的假期(实际未出团)期间没有扣韦唯的工资,却在出国期外的10个月中扣了韦唯的工资。
2、韦唯在扣发工资期间(1990年4月至1991年1月),基本上在团内上班,这是有据可查的,因此,李谷一扣工资理属无故。原告说:1990年全团指令演出88场,韦唯只参加8场,因此应扣韦唯的工资。我们认为,这理由也不能成立:①每场演出不一定都应有韦唯参加;②韦唯的团外公益活动多,正如名医生坐班时间和一般医生就不一样;③轻音乐团管理混乱,无章可循。卷三P50页,1992年5月26日法院办案人员问田玉凤:“上边谈的扣发工资的做法团内有明文规定吗?”田答:“我们团管理混乱,没有什么文字制度,自费出国,团长同意后,交待谁出国了就停发谁的工资。”
法庭上的最后陈述
双方代理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上午的辩论一直持续到午后一点钟,审判长宣布休庭。
原告李谷一在下午的第二轮辩论中,嗓音哽咽,被告汤生午也显得异常激动。双方律师又继续进行了第二轮、第三轮的辩论。旁听席上,成千的听众一次又一次情不自禁地为双方精彩的论辩击掌叫好。
辩论结束后,双方当事人作最后陈述。
“我相信法院会公正处理。”李谷一如是说。
被告汤生午的最后陈述感慨激昂,使不少旁听者落下了眼泪。他在陈述中说:“我原想通过报道使错误的造成者会因此而内疚,然而我想错了,原告不但没有这样,反而更加肆无忌惮地且更大范围地加大对受害者的摧残,更广泛地散发谣言,看来,良好的愿望和良好的结果也许是不一致的。”
被告《声屏周报》主编王根礼在最后陈述中称:对于汤文中个别细节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希望审判长对新闻工作者所受的客观限制予以体谅。
法庭临近结束审理时,审判长询问原告李谷一是否愿意放弃或变更诉讼要求。李谷一说:“很抱歉,不放弃。”审判长再问原告是否愿意接受法庭调解,李谷一说:“由于被告表现不好,不同意调解。”
夜幕来临,审判长再次宣布休庭。
李谷一哭了
1992年7月12日。今天,李谷一名誉权案的一审结局将见分晓。一大早,法庭门外又聚集了数以千计的旁听群众。
直到上午9时30分,法庭才再次开庭。双方当事人在各自的位置上正襟危坐,焦急地等待着法庭的判决。
审判长宣读判决书。判决书很长,大致的意思是,在亚运会演出中,李谷一并未说过韦唯得爱滋病了。至于汤文的其他内容,法庭认为也基本失实。
根据上述认定,审判长宣布:“本庭认为被告报道基本内容失实,损害了原告李谷一的名誉,造成了后果,构成了侵害原告的名誉权。原告诉讼请求理由正当,应予支持”,并认定在这起案件中,《声屏周报》负有主要责任,汤生午“听信一面之词”,也有一定的责任。认为原告李谷一要求被告赔偿16万元损失和支付3000元抚慰金,超过必要合理部分不予支持。
法庭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判决如下:
“一、本院责令被告《声屏周报》和汤生午立即停止对原告李谷一名誉权的侵害;二、被告《声屏周报》和汤生午在《声屏周报》头版显要位置刊登向李谷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文章,所刊文章内容须经本院核准;三、被告《声屏周报》赔偿原告2000元,被告汤生午赔偿原告500元;四、被告《声屏周报》支付原告抚慰金400元,被告汤生午支付原告抚慰金10O元。案件受理费70元由两被告承担。”
听完判决,李谷一激动地哭了,而二位被告人则神情冷峻。旁听席上,没有人们预料中的掌声,这与前两天庭审中的热烈场面显得极不协调。
尽管不服,但未上诉
“这场官司现在还只是划了个逗号,还不是句号。判决并未给我带来喜悦,我的心情是沉重的。到南阳来打官司,我是挺而走险的。由于我的身份、地位,容易使人产生‘大原告、小被告’的想法,如果我赢,会被人认为有背景,如果我输,会被人认为活该。”
听得出,李谷一的语调是伤感的。
“我为这场官司已花了两万多元,因为我珍视艺术家的形象和名誉,这比金钱更宝贵。如果终审维持一审判决的话,我将把赔偿我的3000元捐给南阳的‘希望工程’。”
被告汤生午及《声屏周报》社对法院判决自然不服,但他们表示,这一结果早在意料之中。他们将向河南省高级法院提出上诉。王根礼还表示,如二审维持原判,他将提请检察院抗诉。
被告方的代理人李大进认为:一审判决有失公允,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比如有关爱滋病的传言,已有多人证言证实确系原告所说,虽然“亚运会演出”和“排练”有很大不同,但原告已构成事实并造成后果,这是不容否定的。怎么可以完全抹去呢?离开南阳时,李律师只说了这么一句颇为耐人寻味的话:“以后再不到南阳打官司了!”
被告汤生午的另一位律师窦柏林似乎亦有此同感:“本案结束后将给我的律师生涯划个句号。”
看来,轰动海内外的著名歌唱家李谷一名誉权案的最终结局,似乎还难以预料。但出人意料的是,尽管被告方对法院的判决表示不服,但权衡再三,他们最终未在法定的期限内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个中原因,颇为令人深思。
韦唯道出“临心事”
这场名誉权官司的导火线是在一年多前点燃的。
年1月16日,南阳《声屏周报》头版发表了该报记者汤生午的采访文章,题为《有人说她得了可怕的病,有人干脆说她已经自杀,莫衷一是。著名星韦唯接受本报采访道出其中原因》。文章借韦唯之口,“伤心地道出了她从不愿向外人多讲”的委屈:1、在年亚运会期间的一次演出中,十年前以一曲《乡恋》而名噪内地的某位乐团领导,不知心怀何意但却明显险恶地抓起话筒,向在座各位愤愤宣告了一个大胆的谣言:韦唯得病了。哗然;2、韦唯的工资被无故停发已一年;3、作为国家一级演员,韦唯正常的费这位领导却不准报销;4、分给团里三位演员三套住,其中明确指示要考虑分给韦唯一套。实际结果,不但同韦唯毫不沾边,而且这三套子全上到了该领导个人的户口上;5、国外几家电视台通过对韦唯的演出邀请,在各方都通过的情况下,却被这位领导一人无理拒绝;6、该领导对韦唯说,你走吧,离开这里我们也许才好相处,但走的方式更是其用意“特殊”。她希望韦唯走,一是去国外,二是辞职。如果想调走,那请拿10万元钱来;7、记者的一位同事曾得到过这位领导的明确相告:我就是要整韦唯!怎么了?“党”要整个人还不容易……
文章发表后,《声屏周报》社将报纸寄向与之联网的二百余家地方报纸,并在文章的旁边标明“请转载”字样。到年5月,全国各省数十家报纸先后予以转载。
李谷一聘请律师诉诸
汤文的发表,在社会上掀起轩然,文章发表后,李谷一接连不断地接到质问、质询的和信件;更有恶言相加的辱骂。为了平息风波,为自己正名,李谷一在京召开了有四十多家新闻单位参加的新闻发布会。然后,李谷一又聘请律师为其诉讼代理人,于年1月向南阳地区中级提出诉讼,状告汤生午及《声屏周报》社侵犯其名誉权。
韦唯多变的诉讼地位
本案中,韦唯是个极其关键的人物。因为文章是以韦唯的口吻写的,并且在发表前,又经韦唯两次审稿,内容又都是韦唯的个人经历。因此,如何确认韦唯在案件中的诉讼地位,成了本案的一大难题:证人,第三人,抑或共同被告?如作证人,那案件的胜败与韦唯基本无关;如作第三人,那对韦唯不利,万一汤生午一方败诉,韦唯也只好跟着落败;而如果作为被告,那韦唯败诉后将承担法律责任。但让一个提供消息者承担法律责任,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似乎没有先例,李谷一在起诉书中并未将韦唯列为共同被告也许正是出于这一考虑。然而,南阳地区中级在对本案作了一番调查取证后,于年6月3日决定追加韦唯为共同被告。
韦唯诉讼地位的改变,预示着认为在整个纠纷过程中,韦唯负有一定责任,并有可能承担由此而来的法律后果。并且,韦唯从证人到被告人身份的变化,将使被告一方失去一个至关重要的证人,还使韦唯在法庭上所作的陈述的客观真实性大打折扣。这对被告人汤生午及《声屏周报》社是显然不利的。
但富有戏剧性变化的是,就在开庭的前夕,又突然决定正式撤销韦唯被追加的被告人身份,据云是“依据不足”。
这样,韦唯终于没有走向被告席。但这是否意味着原被告双方在本案中的诉讼命运有了某种转机呢?这仍是一个谜。
扑朔迷离,终于开庭审理
年7月8日,南阳地区中级决定开庭审理本案。
在此之前,曾在就此案进行了调解。就在开庭前夕,在郑州又就此案作了一番调解。但由于双方分歧太大,调解根本无法达成协议。
出人意料的是,就在数百名记者云集宛城、准备采访李谷一名誉权案的庭审经过时,门口又突然贴出了本案延期审理的公告。个中原因.据说是准备就此案进行第三次调解。
两天之后。年7月10,南阳中院又作出了开庭审理的决定。
早晨7点刚过,门口就聚满了前来旁听的众。刚竣工的审判庭,是一座四层楼共多平方米的建筑。正门上方,高悬着耀眼的国徽。四根粗大的黑色大理石柱子,给人以威严。庄重之感,仿佛昭示着法律的神圣。
上午8时30分,薄施粉黛、身着宝蓝色套裙的李谷一在丈夫肖卓能的陪同下来到法庭。被告汤生午、《声屏周报》法定代表人王根礼以及双方的代理律师巩沙、李大进,窦柏林、侯金海等人也先后出庭就坐。
在开庭的前一天,李谷一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表示,面对法庭,她很害怕,这会影响到自己的前半生和后半生。她始终认为汤生午的文章从头到尾都是失实的,正因为这样,她才来打官司。如果汤生午说的基本属实,只是枝节部分有问题,她是不会起诉的。在谈到韦唯时,李谷一说,她不明白韦唯为什么要发这个难,把话说得那么恶。最后,李谷一还对记者表示,如果她确实不对,有错误,她愿意向全国道歉。
在此之前,汤生午也曾信心十足地对记者说:“我认为开庭的话我能胜诉!但最终的结果不是我个人所能决定的。”
原告的指控与被告的答辩
审判长在宣布法庭纪律后,按照法定程序,由原告方宣读起诉书。
李谷一在起诉书中指出:原告方采用或是捏造、或是歪曲的手法,对她的名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这是“”以来演艺界最大的一次事件,是“四人帮”暴虐的重演,她要求被告方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18万元。并且,这个赔偿数额还不包括这次专程来南阳参加诉讼的费用,因为这笔帐目前还无法结算。
针对李谷一的指控,被告汤生午辩称,由于社会上关于韦唯的流传很多,作为一个记者有责任为一个青年演员澄清事实,因而经报社领导同意,对韦唯作了采访。文章写出后两次寄韦唯审查,所写内容都有正确的消息来源。
王根礼主编在答辩时认为,汤生午撰写的是人物专访文章,其基本内容真实。这篇文章在社会上起到了扶正压邪、伸张正义的作用,使外界有关韦唯的谣言消失,韦唯得以重回舞台。他还指责李谷一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身份,召开新闻发布会,向被告方施加压力,使《声屏周报》在上、经济上蒙受重大损失。
紧接着,法庭就汤生午文章所涉及李谷一的内容,依次就李谷一宣告韦唯得病以及在工资、住、费报销、出国演出等非难韦唯的问题逐一进行调查。
上午11时,审判长宣布休庭。
韦唯出庭作证
下午3时,法庭继续开庭审理。
梳着长辫、一身素装的著名星韦唯作为证人被传唤出庭作证。
首先由审判长对韦唯发问。
审判长:“韦唯,你提供的内容与文章是否一致?”
韦唯:“我当时向报社提供的确是这些问题,应该说是一致的。”
审判长:“有否失实的地方?”
韦唯:“李谷一说我得病,是在一次彩排时,而不是在演出时。”
审判长:“关于子问题是怎么回事?”
韦唯:“去老山慰问演出时,我们几个演员向领导提出要求解决住,领导同意批给我们。我回京后打了报告,听说部里批下来几间,其中有我的住。我向李谷一要新钥匙,她拒绝。我得到确切的消息,李谷一得了三套子。”
审判长:“工资问题是怎么回事?”
韦唯:“年6月,我在与李谷一谈话时,她说把我工资停了,我吃惊。李谷一说这样做好管理。我想去领4、5月份的工资,可是从4月份起已经停了,直到现在还停发。”
对于韦唯所作的证词,李谷一当庭表示异议:“韦唯的证词完全不属实!”
韦唯也毫不相让:“我的证词完全属实,我亲身的经历就是证据!”
接着,原告代理律师向韦唯提出了一连串的提问。
下午5时,韦唯作证完毕。
李谷一是否说过韦唯得病?
年7月11日。法庭在经过一天的调查后,进人辩论阶段。
由于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汤生午文章的内容是否属实,而汤文的主要内容是涉及到李谷一是否大庭广众面前散布韦唯得了病。因此,原、被告双方首先就这一问题展开“拉锯战”。
原告代理人认为:年亚运会期间,中国轻音乐团共演出三场,时间是年9月25日至27日晚,地点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参加演出的有关人员及个别观众证实,三场演出中从未出现过李谷一抓过话筒宣布韦唯得病的情节。法庭上,韦唯也承认不是在演出期间,而是在亚运会演出的一次彩排中。并且,有证据证明,当时李谷一只是以询问的语气问她,是出于对韦唯的关心,而根本不像被告人所写的“不知心怀何意但却明显险恶地抓起话筒,向在座各位愤愤宣告了一个大胆的谣言:韦唯得病了。”
对此,被告方代理人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并列举一系列的证据来证明李谷一确在公共场合散布过韦唯得病的谣言。
1、证人韦唯在回答询问时称:“年9月24日排练时,李谷一在台下拿着话筒指挥,我上台时也拿着话筒,我有个习惯爱挠头,当时团长就用话筒说:‘你挠什么头,你那个病掉下来传给别人怎么办?’我听后很别扭,也没吭声。我唱一小节后,就拿着话筒说了一句:‘你还说呢,人家已经告诉我,说是你们俩说出来的(指李谷一夫妇二人)。’我一说,她更厉害了,说:‘谁说的,谁说的?’我说:‘反正有人说。”’
2、卷三P页。证人陈玉生证言:“在年7月份我被抽到亚运全组委会文展部,在演出处工作。……9月24日下午,韦唯上场,右手拿着话筒,从下场门往上场门走时,她的左手挠了挠头,这时李谷一就拿着无线话筒喊:‘韦唯你不要再挠了,别把病掉在舞台上,传染我们团的人。’这时韦唯拿着话筒说:‘我告诉你,李谷一,现在外面说我得病这事都是你给造的谣。’李谷一说:‘谁说的?’韦唯说:‘有三、四个人都告诉我。”’
3、卷三P96页。轻音乐团乐队队长王春生证明说:“韦唯在台上挠脑袋,李说:‘你别老挠脑袋,外边都说你得病了。’接着韦唯说:‘我知道外边说我得病都是你说的。’李说:‘谁说的,叫出来对质。”’
4、原告本人也承认说过此话。在年5月20日调查李谷一笔录中,李说:“韦唯唱第一支后用手挠头(乐队正在找谱子的时候),这时我在台下,我用话筒对韦唯讲:‘韦唯,你别挠了,你现在身体情况怎样,外面传你得了这个病、那个病,你注意一点,别人说你得了病。”’
以上包括李谷一本人在内的共18人(其中原告提供的8个证人)都证明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原告李谷一确实在大庭广众面前说过韦唯得病的话。
但是,原告李谷一却说:“我这样问韦唯是对她的关心。”
所谓有不准确之处,就是在于原告人的话不是在亚运会演出之中,而是在亚运会彩排之时所说。关于这一点,作者汤生午已在《编钟之声》作了纠正。
关于韦唯出国演出
原告代理人指出,整个调查过程中,没有发现“国外几家电视台通过”邀请韦唯出国的有关证据。当然,应该说也就不存在“各方面都通过的情况下却被这位领导一人无理拒绝”的问题。事实是,年9月到10月,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下属的一家录音,曾出面商借韦唯前往爱尔兰演出。为此,轻音乐团领导于10月上旬作了专门研究,表示同意韦唯出国,但有些责任和技术性的问题必须由派出单位承担或解决。团里向部里打了报告,请求批准韦唯出国之行。在这期间,李谷一一直在百忙之中让团里人事处向部里催办,但由于某种客观原因使韦唯这次出国未能成行。从现有的证据看,李谷一对韦唯出国是持积极态度的,并不存在“无理拒绝”的问题。
对此,被告代理人仍认为,汤文的报道是千真万确的。
①卷四P43页有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90)中心发字第文向所作的《关于组织韦唯等三人交流小组出访欧美五国的请示》。
②卷四P45页有我国驻英国、联邦德国、爱尔兰、休斯顿、法国五国文化处表示同意韦唯等三人出访的意见。
③卷四P53-63页有文化交流中心提供的有关韦唯等三人出访的档案材料。
④证人李杰华、马光明证明和其他材料证实,为此事,交流中心先跟艺术局方杰局长说,方杰给李谷一打了,李同意之后,中心向轻音乐团邀请,团里作了正式研究表示同意。
⑤人事处长田玉凤、原党支部书记褚鹤翔、艺术指导刘秉义证明他们和王建国、李谷一共同讨论过韦唯出访事宜,最后的意见是“同意韦唯出国访问”。
⑥艺术局外事处主管此事的冯树龙证明:如果团里明确同意韦唯出国,那我们就根据团里意见,办理政审手续,报外联局。”
以上大量事实证明,对韦唯出国一事,确系各方面都已通过。那么,是否被李谷一无理拒绝呢?以下事实可以说明:
①年10月15日李谷一曾以轻音乐团的名义为阻止韦唯出国向艺术局发了《关于外单位借调我团韦唯出国的情况请示》。李在请示中写到:“……对此事我们感到相当为难,……对韦唯目前的思想和身体状况,我们不无担心。”报告中还具体写了韦唯思想不好的表现。报告自始至终没有表明“团里同意韦唯出国”的意见。这是个不同意韦唯出国的报告。
②卷三P8页。年5月19日李杰华证明说:“……李谷一隐瞒了一个事实,就是没有把团里确定的情况汇报给艺术局,局领导认为,轻音乐团对韦唯外出一事态度不明。李谷一是有责任的。”
③卷三P18页。年5月29日马文光证明:乐团支部大会开会同意韦唯出国。李谷一个人给艺术局打的报告没有证明同意韦唯出国。这个报告是李谷一以个人名义(注:盖的是团印)给艺术局写的建议。没有把大会通过的“同意韦唯出国”的决定报给艺术局。杰华老师明确指出她这个做法是错误的。”
④卷四P74页。年6月6日,音像出版社副社长,出国组组长江凌证明:“当时韦唯跟我谈到李谷一可能有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出面和李谷一协商,李谷一提出三条意见:第一,韦唯表现不好;第二,韦唯身体不好:第三.由交流中心支付一部分停演费。”
汤文说,李谷一“一人无理拒绝”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韦唯的分问题
原告代理人指出,据管部门证实,年元月下旬,将五套住借给轻音乐团使用。地点是西坝河。这五套子的分配权属于轻音乐团。其中两套做临时办公室,另三套分配给韦唯、鞠敬伟、黄卓三位女演员。不知何种原因,韦唯对所分住不满意,拒绝在住协议卜签字,因此没有住进去。不过,到目前为止,该套住还仍为韦唯保留。计财司产处证实:“西坝河三楼为产总的商品,计财司预先与产总办理有关契约手续时,在办理轻音乐团的五套住时,是我们用李谷一团长的名字签订了临时协议,为了单位领导承担应有的权利和义务,与李谷一同志的户口不发生任何牵连。”该部门还证明,“从来不干涉所属院团的分方案,中国轻音乐团的住问题由该团自定。”由此,三个问题大白于天下:其一,并不是李谷一没有给韦唯住,而是她自己不知何故没有办理居住手续;其二,从来没有“明确指示”要分给韦唯一套住,而分由团里自行决定;其三,并不是“三套子全上到了该领导个人的户口上”,而是有关部门用李谷一的名字去办理了屋归属的有关手续。是履行法定代表人的义务,是一种签字保证,与李谷一个人户口“毫不沾边”。
被告代理人认为,汤文关于韦唯住问题上的内容,其基本事实是存在的,根据是:1、年5月22日韦唯回答询问时说:“……××部长指示子给我们三个人,此事我是后来跟艺术局领导谈话时知道的(是艺术局领导给计财司打我听到的)。高部长替我打让给我一套。李谷一跟我说有我一套,但没有给我住。我多次向李谷一要求,李说:‘你等着,等着,你不是要出国吗?’‘你的问题很多,以后再说。’“问韦唯:“你的住手续办没有?”韦唯答:“没有,她不理我,她不给我,她说:‘你不是要出国吗,出了国再说。’我总是遭到拒绝。”
2、计财司甄司长。艺术局党组办公室白主任证明:韦唯上述的证词是准确的。甄司长讲:“两年前,从西坝河给他们几套子,当时口头上给李谷一说过给几个演员(韦唯、黄卓、鞠敬伟)考虑一下。分时计财司没有文字戴帽,团里是怎样分的我们不了解。后来产处汇报说:‘李谷一反映韦唯要出国,子先不给她。”’
3、从管部门一整套有关三套子分配的档案材料来看,这三套子确实记在了李谷一名下。
“无故扣发韦唯工资”
关于汤文所称无故扣发韦唯工资一事,原告代理人指出:
年12月27日,批准了韦唯提出的自费赴瑞士旅游访友的申请。根据国家的有关政策,的批复函中的确指示中国轻音乐团,对韦唯“假期期间停发工资”(见艺人字[89]第函)。不知什么原因,韦唯未能出国,但也一直未到团里销假报到;近一年的时间与单位脱离。中国轻音乐团根据、以及团里的制度、规定,无正当理由逾假不归,可以停发工资或依旷职论,故此停发了韦唯工资。但停发的是10个月(截止到汤文发表之日)而不是一年。
被告代理人认为,李谷一的这一做法仍有不当之处。
1、年12月27日艺人字(89)第《关于同意韦唯自费赴瑞士旅游的批复》称:“同意你团韦唯应黛安娜女士邀请自费赴瑞士旅游访友三个月,假期期间停发工资……”。而李谷一在3个月的假期(实际未出团)期间没有扣韦唯的工资,却在出国期外的10个月中扣了韦唯的工资。
2、韦唯在扣发工资期间(年4月至年1月),基本上在团内上班,这是有据可查的,因此,李谷一扣工资理属无故。原告说:年全团指令演出88场,韦唯只参加8场,因此应扣韦唯的工资。我们认为,这理由也不能成立:①每场演出不一定都应有韦唯参加;②韦唯的团外公益活动多,正如名坐班时间和一般就不一样;③轻音乐团管理混乱,无章可循。卷三P50页,年5月26日办案人员问田玉凤:“上边谈的扣发工资的做法团内有明文规定吗?”田答:“我们团管理混乱,没有什么文字制度,自费出国,团长同意后,交待谁出国了就停发谁的工资。”
法庭上的最后陈述
双方代理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上午的辩论一直持续到午后一点钟,审判长宣布休庭。
原告李谷一在下午的第二轮辩论中,嗓音哽咽,被告汤生午也显得异常激动。双方律师又继续进行了第二轮、第三轮的辩论。旁听席上,成千的听众一次又一次情不自禁地为双方精彩的论辩击掌叫好。
辩论结束后,双方当事人作最后陈述。
“我相信会公正处理。”李谷一如是说。
被告汤生午的最后陈述感慨激昂,使不少旁听者落下了眼泪。他在陈述中说:“我原想通过报道使错误的造成者会因此而内疚,然而我想错了,原告不但没有这样,反而更加肆无忌惮地且更大范围地加大对受害者的摧残,更广泛地散发谣言,看来,良好的愿望和良好的结果也许是不一致的。”
被告《声屏周报》主编王根礼在最后陈述中称:对于汤文中个别细节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希望审判长对新闻工作者所受的客观限制予以体谅。
法庭临近结束审理时,审判长询问原告李谷一是否愿意放弃或变更诉讼要求。李谷一说:“很抱歉,不放弃。”审判长再问原告是否愿意接受法庭调解,李谷一说:“由于被告表现不好,不同意调解。”
夜幕来临,审判长再次宣布休庭。
李谷一哭了
年7月12日。今天,李谷一名誉权案的一审结局将见分晓。一大早,法庭门外又聚集了数以千计的旁听众。
直到上午9时30分,法庭才再次开庭。双方当事人在各自的位置上正襟危坐,焦急地等待着法庭的判决。
审判长宣读判决书。判决书很长,大致的意思是,在亚运会演出中,李谷一并未说过韦唯得病了。至于汤文的其他内容,法庭认为也基本失实。
根据上述认定,审判长宣布:“本庭认为被告报道基本内容失实,损害了原告李谷一的名誉,造成了后果,构成了侵害原告的名誉权。原告诉讼请求理由正当,应予支持”,并认定在这起案件中,《声屏周报》负有主要责任,汤生午“听信一面之词”,也有一定的责任。认为原告李谷一要求被告赔偿16万元损失和支付元抚慰金,超过必要合理部分不予支持。
法庭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判决如下:
“一、本院责令被告《声屏周报》和汤生午立即停止对原告李谷一名誉权的侵害;二、被告《声屏周报》和汤生午在《声屏周报》头版显要位置刊登向李谷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文章,所刊文章内容须经本院核准;三、被告《声屏周报》赔偿原告元,被告汤生午赔偿原告元;四、被告《声屏周报》支付原告抚慰金元,被告汤生午支付原告抚慰金10O元。案件受理费70元由两被告承担。”
听完判决,李谷一激动地哭了,而二位被告人则神情冷峻。旁听席上,没有人们预料中的掌声,这与前两天庭审中的热烈场面显得极不协调。
尽管不服,但未上诉
“这场官司现在还只是划了个逗,还不是句。判决并未给我带来喜悦,我的心情是沉重的。到南阳来打官司,我是挺而走险的。由于我的身份、地位,容易使人产生‘大原告、小被告’的想法,如果我赢,会被人认为有背景,如果我输,会被人认为活该。”
听得出,李谷一的语调是伤感的。
“我为这场官司已花了两万多元,因为我珍视艺术家的形象和名誉,这比金钱更宝贵。如果终审维持一审判决的话,我将把赔偿我的元捐给南阳的‘希望工程’。”
被告汤生午及《声屏周报》社对判决自然不服,但他们表示,这一结果早在意料之中。他们将向河南省高级提出上诉。王根礼还表示,如二审维持原判,他将提请检察院抗诉。
被告方的代理人李大进认为:一审判决有失公允,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比如有关病的传言,已有多人证言证实确系原告所说,虽然“亚运会演出”和“排练”有很大不同,但原告已构成事实并造成后果,这是不容否定的。怎么可以完全抹去呢?离开南阳时,李律师只说了这么一句颇为耐人寻味的话:“以后再不到南阳打官司了!”
被告汤生午的另一位律师窦柏林似乎亦有此同感:“本案结束后将给我的律师生涯划个句。”
看来,轰动海内外的著名唱家李谷一名誉权案的最终结局,似乎还难以预料。但出人意料的是,尽管被告方对的判决表示不服,但权衡再三,他们最终未在法定的期限内上诉于河南省高级。
个中原因,颇为令人深思。
我也是才看了全部内容,虽然李谷一胜诉,但看过了经过感觉李谷一老师当年确实有些要压人一等的气势,有些事情未能客观处理,而是显得有些偏激
1991年1月16日,南阳《声屏周报》头版发表了该报记者汤生午的采访文章,题为《有人说她得了可怕的病,有人干脆说她已经自杀,舆论莫衷一是。著名歌星韦唯接受本报电话采访道出其中原因》。文章借韦唯之口,“伤心地道出了她从不愿向外人多讲”的委屈:1、在1990年亚运会期间的一次演出中,十年前以一曲《乡恋》而名噪内地的某位乐团领导,不知心怀何意但却明显险恶地抓起话筒,向在座各位愤愤宣告了一个大胆的谣言:韦唯得爱滋病了。舆论哗然;2、韦唯的工资被无故停发已一年;3、作为国家一级演员,韦唯正常的医疗费这位领导却不准报销;4、文化部分给团里三位演员三套住房,其中明确指示要考虑分给韦唯一套。实际结果,不但同韦唯毫不沾边,而且这三套房子全上到了该领导个人的户口上;5、国外几家电视台通过文化部对韦唯的演出邀请,在各方都通过的情况下,却被这位领导一人无理拒绝;6、该领导对韦唯说,你走吧,离开这里我们也许才好相处,但走的方式更是其用意“特殊”。她希望韦唯走,一是去国外,二是辞职。如果想调走,那请拿10万元钱来;7、记者的一位同事曾得到过这位领导的明确相告:我就是要整韦唯!怎么了?“***”要整个人还不容易……
文章发表后,《声屏周报》社将报纸寄向与之联网的二百余家地方报纸,并在文章的旁边标明“请转载”字样。到1991年5月,全国各省市数十家报纸先后予以转载。
李谷一聘请律师诉诸法院
汤文的发表,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文章发表后,李谷一接连不断地接到质问、质询的电话和信件;更有恶言相加的辱骂。为了平息风波,为自己正名,李谷一在京召开了有四十多家新闻单位参加的新闻发布会。然后,李谷一又聘请律师为其诉讼代理人,于1992年1月向南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状告汤生午及《声屏周报》社侵犯其名誉权。
韦唯多变的诉讼地位
本案中,韦唯是个极其关键的人物。因为文章是以韦唯的口吻写的,并且在发表前,又经韦唯两次审稿,内容又都是韦唯的个人经历。因此,如何确认韦唯在案件中的诉讼地位,成了本案的一大难题:证人,第三人,抑或共同被告?如作证人,那案件的胜败与韦唯基本无关;如作第三人,那对韦唯不利,万一汤生午一方败诉,韦唯也只好跟着落败;而如果作为被告,那韦唯败诉后将承担法律责任。但让一个提供消息者承担法律责任,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似乎没有先例,李谷一在起诉书中并未将韦唯列为共同被告也许正是出于这一考虑。然而,南阳地区中级法院在对本案作了一番调查取证后,于1992年6月3日决定追加韦唯为共同被告。
韦唯诉讼地位的改变,预示着法院认为在整个纠纷过程中,韦唯负有一定责任,并有可能承担由此而来的法律后果。并且,韦唯从证人到被告人身份的变化,将使被告一方失去一个至关重要的证人,还使韦唯在法庭上所作的陈述的客观真实性大打折扣。这对被告人汤生午及《声屏周报》社是显然不利的。
但富有戏剧性变化的是,就在开庭的前夕,法院又突然决定正式撤销韦唯被追加的被告人身份,据云是“依据不足”。
这样,韦唯终于没有走向被告席。但这是否意味着原被告双方在本案中的诉讼命运有了某种转机呢?这仍是一个谜。
扑朔迷离,法院终于开庭审理
1992年7月8日,南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理本案。
在此之前,法院曾在北京就此案进行了调解。就在开庭前夕,法院在郑州又就此案作了一番调解。但由于双方分歧太大,调解根本无法达成协议。
出人意料的是,就在数百名记者云集宛城、准备采访李谷一名誉权案的庭审经过时,法院门口又突然贴出了本案延期审理的公告。个中原因.据说是法院准备就此案进行第三次调解。
两天之后。1992年7月10,南阳中院又作出了开庭审理的决定。
早晨7点刚过,法院门口就聚满了前来旁听的群众。刚竣工的审判庭,是一座四层楼共2500多平方米的建筑。正门上方,高悬着耀眼的国徽。四根粗大的黑色大理石柱子,给人以威严。庄重之感,仿佛昭示着法律的神圣。
上午8时30分,薄施粉黛、身着宝蓝色套裙的李谷一在丈夫肖卓能的陪同下来到法庭。被告汤生午、《声屏周报》法定代表人王根礼以及双方的代理律师巩沙、李大进,窦柏林、侯金海等人也先后出庭就坐。
在开庭的前一天,李谷一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表示,面对法庭,她很害怕,这会影响到自己的前半生和后半生。她始终认为汤生午的文章从头到尾都是失实的,正因为这样,她才来打官司。如果汤生午说的基本属实,只是枝节部分有问题,她是不会起诉的。在谈到韦唯时,李谷一说,她不明白韦唯为什么要发这个难,把话说得那么恶。最后,李谷一还对记者表示,如果她确实不对,有错误,她愿意向全国人民道歉。
在此之前,汤生午也曾信心十足地对记者说:“我认为开庭的话我能胜诉!但最终的结果不是我个人所能决定的。”
原告的指控与被告的答辩
审判长在宣布法庭纪律后,按照法定程序,由原告方宣读起诉书。
李谷一在起诉书中指出:原告方采用或是捏造、或是歪曲的手法,对她的名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这是“文革”以来演艺界最大的一次事件,是“四人帮”暴虐的重演,她要求被告方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18万元。并且,这个赔偿数额还不包括这次专程来南阳参加诉讼的费用,因为这笔帐目前还无法结算。
针对李谷一的指控,被告汤生午辩称,由于社会上关于韦唯的流传很多,作为一个记者有责任为一个青年演员澄清事实,因而经报社领导同意,对韦唯作了电话采访。文章写出后两次寄韦唯审查,所写内容都有正确的消息来源。
王根礼主编在答辩时认为,汤生午撰写的是人物专访文章,其基本内容真实。这篇文章在社会上起到了扶正压邪、伸张正义的作用,使外界有关韦唯的谣言消失,韦唯得以重回舞台。他还指责李谷一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身份,召开新闻发布会,向被告方施加压力,使《声屏周报》在政治上、经济上蒙受重大损失。
紧接着,法庭就汤生午文章所涉及李谷一的内容,依次就李谷一宣告韦唯得爱滋病以及在工资、住房、医疗费报销、出国演出等非难韦唯的问题逐一进行调查。
上午11时,审判长宣布休庭。
韦唯出庭作证
下午3时,法庭继续开庭审理。
梳着长辫、一身素装的著名歌星韦唯作为证人被传唤出庭作证。
首先由审判长对韦唯发问。
审判长:“韦唯,你提供的内容与文章是否一致?”
韦唯:“我当时向报社提供的确是这些问题,应该说是一致的。”
审判长:“有否失实的地方?”
韦唯:“李谷一说我得爱滋病,是在一次彩排时,而不是在演出时。”
审判长:“关于房子问题是怎么回事?”
韦唯:“去老山慰问演出时,我们几个演员向文化部领导提出要求解决住房,领导同意批给我们。我回京后打了报告,听说部里批下来几间房,其中有我的住房。我向李谷一要新房钥匙,她拒绝。我得到确切的消息,李谷一得了三套房子。”
审判长:“工资问题是怎么回事?”
韦唯:“1990年6月,我在与李谷一谈话时,她说把我工资停了,我吃惊。李谷一说这样做好管理。我想去领4、5月份的工资,可是从4月份起已经停了,直到现在还停发。”
对于韦唯所作的证词,李谷一当庭表示异议:“韦唯的证词完全不属实!”
韦唯也毫不相让:“我的证词完全属实,我亲身的经历就是证据!”
接着,原告代理律师向韦唯提出了一连串的提问。
下午5时,韦唯作证完毕。
李谷一是否说过韦唯得爱滋病?
1992年7月11日。法庭在经过一天的调查后,进人辩论阶段。
由于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汤生午文章的内容是否属实,而汤文的主要内容是涉及到李谷一是否大庭广众面前散布韦唯得了爱滋病。因此,原、被告双方首先就这一问题展开“拉锯战”。
原告代理人认为:1990年亚运会期间,中国轻音乐团共演出三场,时间是1990年9月25日至27日晚,地点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参加演出的有关人员及个别观众证实,三场演出中从未出现过李谷一抓过话筒宣布韦唯得爱滋病的情节。法庭上,韦唯也承认不是在演出期间,而是在亚运会演出的一次彩排中。并且,有证据证明,当时李谷一只是以询问的语气问她,是出于对韦唯的关心,而根本不像被告人所写的“不知心怀何意但却明显险恶地抓起话筒,向在座各位愤愤宣告了一个大胆的谣言:韦唯得爱滋病了。”
对此,被告方代理人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并列举一系列的证据来证明李谷一确在公共场合散布过韦唯得爱滋病的谣言。
1、证人韦唯在回答法院询问时称:“1990年9月24日排练时,李谷一在台下拿着话筒指挥,我上台时也拿着话筒,我有个习惯爱挠头,当时团长就用话筒说:‘你挠什么头,你那个爱滋病掉下来传给别人怎么办?’我听后很别扭,也没吭声。我唱一小节后,就拿着话筒说了一句:‘你还说呢,人家已经告诉我,说是你们俩说出来的(指李谷一夫妇二人)。’我一说,她更厉害了,说:‘谁说的,谁说的?’我说:‘反正有人说。”’
2、卷三P178页。证人陈玉生证言:“在1990年7月份我被抽到亚运全组委会文展部,在演出处工作。……9月24日下午,韦唯上场,右手拿着话筒,从下场门往上场门走时,她的左手挠了挠头,这时李谷一就拿着无线话筒喊:‘韦唯你不要再挠了,别把爱滋病掉在舞台上,传染我们团的人。’这时韦唯拿着话筒说:‘我告诉你,李谷一,现在外面说我得爱滋病这事都是你给造的谣。’李谷一说:‘谁说的?’韦唯说:‘有三、四个人都告诉我。”’
3、卷三P96页。轻音乐团乐队队长王春生证明说:“韦唯在台上挠脑袋,李说:‘你别老挠脑袋,外边都说你得爱滋病了。’接着韦唯说:‘我知道外边说我得爱滋病都是你说的。’李说:‘谁说的,叫出来对质。”’
4、原告本人也承认说过此话。在1992年5月20日法院调查李谷一笔录中,李说:“韦唯唱第一支歌后用手挠头(乐队正在找谱子的时候),这时我在台下,我用话筒对韦唯讲:‘韦唯,你别挠了,你现在身体情况怎样,外面传你得了这个病、那个病,你注意一点,别人说你得了爱滋病。”’
以上包括李谷一本人在内的共18人(其中原告提供的8个证人)都证明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原告李谷一确实在大庭广众面前说过韦唯得爱滋病的话。
但是,原告李谷一却说:“我这样问韦唯是对她的关心。”
所谓有不准确之处,就是在于原告人的话不是在亚运会演出之中,而是在亚运会彩排之时所说。关于这一点,作者汤生午已在《编钟之声》作了纠正。
关于韦唯出国演出
原告代理人指出,整个调查过程中,没有发现“国外几家电视台通过文化部”邀请韦唯出国的有关证据。当然,应该说也就不存在“各方面都通过的情况下却被这位领导一人无理拒绝”的问题。事实是,1990年9月到10月,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下属的一家录音公司,曾出面商借韦唯前往爱尔兰演出。为此,轻音乐团领导于10月上旬作了专门研究,表示同意韦唯出国,但有些责任和技术性的问题必须由派出单位承担或解决。团里向部里打了报告,请求批准韦唯出国之行。在这期间,李谷一一直在百忙之中让团里人事处向部里催办,但由于某种客观原因使韦唯这次出国未能成行。从现有的证据看,李谷一对韦唯出国是持积极态度的,并不存在“无理拒绝”的问题。
对此,被告代理人仍认为,汤文的报道是千真万确的。
①卷四P43页有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90)中心发字第112号文向文化部所作的《关于组织韦唯等三人交流小组出访欧美五国的请示》。
②卷四P45页有我国驻英国、联邦德国、爱尔兰、休斯顿、法国五国使馆文化处表示同意韦唯等三人出访的意见。
③卷四P53-63页有文化交流中心提供的有关韦唯等三人出访的档案材料。
④证人李杰华、马光明证明和其他材料证实,为此事,交流中心先跟文化部艺术局方杰局长说,方杰给李谷一打了电话,李同意之后,中心向轻音乐团邀请,团里作了正式研究表示同意。
⑤人事处长田玉凤、原党支部书记褚鹤翔、艺术指导刘秉义证明他们和王建国、李谷一共同讨论过韦唯出访事宜,最后的意见是“同意韦唯出国访问”。
⑥艺术局外事处主管此事的冯树龙证明:如果团里明确同意韦唯出国,那我们就根据团里意见,办理政审手续,报外联局。”
以上大量事实证明,对韦唯出国一事,确系各方面都已通过。那么,是否被李谷一无理拒绝呢?以下事实可以说明:
①1991年10月15日李谷一曾以轻音乐团的名义为阻止韦唯出国向文化部艺术局发了《关于外单位借调我团韦唯出国的情况请示》。李在请示中写到:“……对此事我们感到相当为难,……对韦唯目前的思想和身体状况,我们不无担心。”报告中还具体写了韦唯思想不好的表现。报告自始至终没有表明“团里同意韦唯出国”的意见。这是个不同意韦唯出国的报告。
②卷三P8页。1992年5月19日李杰华证明说:“……李谷一隐瞒了一个事实,就是没有把团里确定的情况汇报给艺术局,局领导认为,轻音乐团对韦唯外出一事态度不明。李谷一是有责任的。”
③卷三P18页。1992年5月29日马文光证明:乐团支部大会开会同意韦唯出国。李谷一个人给艺术局打的报告没有证明同意韦唯出国。这个报告是李谷一以个人名义(注:盖的是团印)给艺术局写的建议。没有把大会通过的“同意韦唯出国”的决定报给艺术局。杰华老师明确指出她这个做法是错误的。”
④卷四P74页。1992年6月6日,音像出版社副社长,出国组组长江凌证明:“当时韦唯跟我谈到李谷一可能有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出面和李谷一协商,李谷一提出三条意见:第一,韦唯表现不好;第二,韦唯身体不好:第三.由交流中心支付一部分停演费。”
汤文说,李谷一“一人无理拒绝”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韦唯的分房问题
原告代理人指出,据文化部房管部门证实,1990年元月下旬,文化部将五套住房借给轻音乐团使用。地点是北京西坝河。这五套房子的分配权属于轻音乐团。其中两套做临时办公室,另三套分配给韦唯、鞠敬伟、黄卓三位女演员。不知何种原因,韦唯对所分住房不满意,拒绝在住房协议卜签字,因此没有住进去。不过,到目前为止,该套住房还仍为韦唯保留。文化部计财司房产处证实:“西坝河三号楼为北京市房产开发总公司的商品房,文化部计财司预先与房产总公司办理有关契约手续时,在办理轻音乐团的五套住房时,是我们用李谷一团长的名字签订了临时协议,为了单位领导承担应有的权利和义务,与李谷一同志的户口不发生任何牵连。”该部门还证明,“文化部从来不干涉所属院团的分房方案,中国轻音乐团的住房问题由该团自定。”由此,三个问题大白于天下:其一,并不是李谷一没有给韦唯住房,而是她自己不知何故没有办理居住手续;其二,文化部从来没有“明确指示”要分给韦唯一套住房,而分房由团里自行决定;其三,并不是“三套房子全上到了该领导个人的户口上”,而是文化部有关部门用李谷一的名字去办理了房屋归属的有关手续。是履行法定代表人的义务,是一种签字保证,与李谷一个人户口“毫不沾边”。
被告代理人认为,汤文关于韦唯住房问题上的内容,其基本事实是存在的,根据是:1、1992年5月22日韦唯回答法院询问时说:“……文化部××部长指示房子给我们三个人,此事我是后来跟艺术局领导谈话时知道的(是艺术局领导给计财司打电话我听到的)。高部长替我打电话让给我一套。李谷一跟我说有我一套,但没有给我住。我多次向李谷一要求,李说:‘你等着,等着,你不是要出国吗?’‘你的问题很多,以后再说。’“法院问韦唯:“你的住房手续办没有?”韦唯答:“没有,她不理我,她不给我,她说:‘你不是要出国吗,出了国再说。’我总是遭到拒绝。”
2、文化部计财司甄司长。艺术局党组办公室白主任证明:韦唯上述的证词是准确的。甄司长讲:“两年前,从西坝河给他们几套房子,当时口头上给李谷一说过给几个演员(韦唯、黄卓、鞠敬伟)考虑一下。分房时计财司没有文字戴帽,团里是怎样分的我们不了解。后来房产处汇报说:‘李谷一反映韦唯要出国,房子先不给她。”’
3、从房管部门一整套有关三套房子分配的档案材料来看,这三套房子确实记在了李谷一名下。
“无故扣发韦唯工资”
关于汤文所称无故扣发韦唯工资一事,原告代理人指出:
1989年12月27日,文化部批准了韦唯提出的自费赴瑞士旅游访友的申请。根据国家的有关政策,文化部的批复函中的确指示中国轻音乐团,对韦唯“假期期间停发工资”(见文化部艺人字[89]第326号函)。不知什么原因,韦唯未能出国,但也一直未到团里销假报到;近一年的时间与单位脱离联系。中国轻音乐团根据文化部、北京市以及团里的制度、规定,无正当理由逾假不归,可以停发工资或依旷职论,故此停发了韦唯工资。但停发的是10个月(截止到汤文发表之日)而不是一年。
被告代理人认为,李谷一的这一做法仍有不当之处。
1、1989年12月27日文化部艺人字(89)第326号《关于同意韦唯自费赴瑞士旅游的批复》称:“同意你团韦唯应黛安娜女士邀请自费赴瑞士旅游访友三个月,假期期间停发工资……”。而李谷一在3个月的假期(实际未出团)期间没有扣韦唯的工资,却在出国期外的10个月中扣了韦唯的工资。
2、韦唯在扣发工资期间(1990年4月至1991年1月),基本上在团内上班,这是有据可查的,因此,李谷一扣工资理属无故。原告说:1990年全团指令演出88场,韦唯只参加8场,因此应扣韦唯的工资。我们认为,这理由也不能成立:①每场演出不一定都应有韦唯参加;②韦唯的团外公益活动多,正如名医生坐班时间和一般医生就不一样;③轻音乐团管理混乱,无章可循。卷三P50页,1992年5月26日法院办案人员问田玉凤:“上边谈的扣发工资的做法团内有明文规定吗?”田答:“我们团管理混乱,没有什么文字制度,自费出国,团长同意后,交待谁出国了就停发谁的工资。”
法庭上的最后陈述
双方代理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上午的辩论一直持续到午后一点钟,审判长宣布休庭。
原告李谷一在下午的第二轮辩论中,嗓音哽咽,被告汤生午也显得异常激动。双方律师又继续进行了第二轮、第三轮的辩论。旁听席上,成千的听众一次又一次情不自禁地为双方精彩的论辩击掌叫好。
辩论结束后,双方当事人作最后陈述。
“我相信法院会公正处理。”李谷一如是说。
被告汤生午的最后陈述感慨激昂,使不少旁听者落下了眼泪。他在陈述中说:“我原想通过报道使错误的造成者会因此而内疚,然而我想错了,原告不但没有这样,反而更加肆无忌惮地且更大范围地加大对受害者的摧残,更广泛地散发谣言,看来,良好的愿望和良好的结果也许是不一致的。”
被告《声屏周报》主编王根礼在最后陈述中称:对于汤文中个别细节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希望审判长对新闻工作者所受的客观限制予以体谅。
法庭临近结束审理时,审判长询问原告李谷一是否愿意放弃或变更诉讼要求。李谷一说:“很抱歉,不放弃。”审判长再问原告是否愿意接受法庭调解,李谷一说:“由于被告表现不好,不同意调解。”
夜幕来临,审判长再次宣布休庭。
李谷一哭了
1992年7月12日。今天,李谷一名誉权案的一审结局将见分晓。一大早,法庭门外又聚集了数以千计的旁听群众。
直到上午9时30分,法庭才再次开庭。双方当事人在各自的位置上正襟危坐,焦急地等待着法庭的判决。
审判长宣读判决书。判决书很长,大致的意思是,在亚运会演出中,李谷一并未说过韦唯得爱滋病了。至于汤文的其他内容,法庭认为也基本失实。
根据上述认定,审判长宣布:“本庭认为被告报道基本内容失实,损害了原告李谷一的名誉,造成了后果,构成了侵害原告的名誉权。原告诉讼请求理由正当,应予支持”,并认定在这起案件中,《声屏周报》负有主要责任,汤生午“听信一面之词”,也有一定的责任。认为原告李谷一要求被告赔偿16万元损失和支付3000元抚慰金,超过必要合理部分不予支持。
法庭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判决如下:
“一、本院责令被告《声屏周报》和汤生午立即停止对原告李谷一名誉权的侵害;二、被告《声屏周报》和汤生午在《声屏周报》头版显要位置刊登向李谷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文章,所刊文章内容须经本院核准;三、被告《声屏周报》赔偿原告2000元,被告汤生午赔偿原告500元;四、被告《声屏周报》支付原告抚慰金400元,被告汤生午支付原告抚慰金10O元。案件受理费70元由两被告承担。”
听完判决,李谷一激动地哭了,而二位被告人则神情冷峻。旁听席上,没有人们预料中的掌声,这与前两天庭审中的热烈场面显得极不协调。
尽管不服,但未上诉
“这场官司现在还只是划了个逗号,还不是句号。判决并未给我带来喜悦,我的心情是沉重的。到南阳来打官司,我是挺而走险的。由于我的身份、地位,容易使人产生‘大原告、小被告’的想法,如果我赢,会被人认为有背景,如果我输,会被人认为活该。”
听得出,李谷一的语调是伤感的。
“我为这场官司已花了两万多元,因为我珍视艺术家的形象和名誉,这比金钱更宝贵。如果终审维持一审判决的话,我将把赔偿我的3000元捐给南阳的‘希望工程’。”
被告汤生午及《声屏周报》社对法院判决自然不服,但他们表示,这一结果早在意料之中。他们将向河南省高级法院提出上诉。王根礼还表示,如二审维持原判,他将提请检察院抗诉。
被告方的代理人李大进认为:一审判决有失公允,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比如有关爱滋病的传言,已有多人证言证实确系原告所说,虽然“亚运会演出”和“排练”有很大不同,但原告已构成事实并造成后果,这是不容否定的。怎么可以完全抹去呢?离开南阳时,李律师只说了这么一句颇为耐人寻味的话:“以后再不到南阳打官司了!”
被告汤生午的另一位律师窦柏林似乎亦有此同感:“本案结束后将给我的律师生涯划个句号。”
看来,轰动海内外的著名歌唱家李谷一名誉权案的最终结局,似乎还难以预料。但出人意料的是,尽管被告方对法院的判决表示不服,但权衡再三,他们最终未在法定的期限内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个中原因,颇为令人深思。
